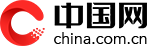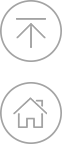2021年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本书编制了2000—2019年共计2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摸清家底”,从存量的角度把握这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向。
中国社会总资产已经由2017年的接近1400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655.6万亿元。考虑到2019年的社会总负债达到980.1万亿元,则社会净财富为675.5万亿元,人均社会净财富约为48.2万元。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居民人均财富约为36.6万元。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GDP已经由2000年的10万亿元,攀升到2019年的接近100万亿元;而财富存量由2000年的不到39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75.5万亿元。2000—2019年,中国名义GDP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2.8%,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6.2%。财富增速快于名义GDP增速(更快于实际GDP增速)。由于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存量赶超”。
财富规模演进
财富相较GDP,在衡量一国综合实力方面无疑更具代表性。就2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财富规模大幅增长,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从社会净财富由国内非金融资产和对外净资产的构成来看:国内非金融资产由2000年的38.4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61.9万亿元;国内非金融资产是社会净财富的主体,2019年占比高达98%。对外净资产由2000年的0.48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3.6万亿元;对外净资产为正且具有一定的规模,意味着就全球而言,中国是净储蓄的提供者。从社会净财富由政府部门净资产与居民部门净资产的构成来看:广义政府净资产由2000年的8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40万亿元,由2015年的刚刚超过100万亿元,到2019年的162.8万亿元;居民部门净资产由2000年的30.6万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100万亿元,2011年的200万亿元,2014年的近300万亿元,2017年的400万亿元,直至2019年的512.6万亿元。
中美财富比较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书以2018年的数据作比较(中国的数据已经更新到2019年)。其中,中国的GDP占美国的65%,社会净财富占美国的80%。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但2009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逆转,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存量赶超,除了经济快速增长加上高储蓄、高投资,也包含价值重估因素。后者除了一般资产价格变动,还有人民币汇率变动。
考虑到各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在进行财富国际比较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仅就中美情况而言,两国间的财富比较就面临非金融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处理方法不一致的问题。具体来说,美国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估算当中,将居民及非营利机构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持有的建筑物与土地价值合并计算未做拆分。但在处理金融部门、联邦政府部门和州政府部门时,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美国方面选择了只计算地面建筑物价值而忽略了土地价值。从可比性角度,如果我们将国有建设用地价值扣除(2018年为31.5万亿元,约合4.6亿美元),那么,2018年中国的财富规模将缩减为84万亿美元,占美国财富的比重由原来的80%,下降为76%。上述分析表明:第一,关于财富的估算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相对而言,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更加可靠,接受度也更高。第二,财富估算方法取决于考察的视角。包容性财富估算以及其他方法,是对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的一个补充,这使得我们利用后者进行财富比较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尽管如此,以财富来衡量的中国综合国力处于世界第二位,而且比GDP所显示的更接近美国的实力,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不过,考虑到中国人口差不多是美国的4.3倍,因此,尽管从全社会角度,中国财富占美国的80%(扣除土地价值,占比为76%),但从人均角度看,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还不到20%。
财富积累
中国近20年来社会净财富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中国社会净财富相对于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贡献:较高的储蓄率和价值重估效应。较高的储蓄率直接对应较高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各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带来了非金融资产的每期增量。在每期的总产出中,消费占比相对较小,而投资占比相对较大,促进了中国财富总量的更快增长。财富总量上涨的另一个因素是价值重估过程——土地增值、股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均促进了存量资产的市场价值上升。
财富分配
2019年,中国675.5万亿元的社会净财富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占比为76%;政府部门财富为162.8万亿元,占比为24%。从时间序列来看,居民财富占比呈现波动,2000—2005年呈上升态势,2006—2011年呈下降态势,2012—2019年又呈上升态势。2000—2009年居民财富平均占比为78.4%,而2010—2019年平均占比下降为75.2%。因此,从21世纪的前10年与后10年比较来看,居民财富占比下降了2.8个百分点。与发达经济体迥异的财富分配结构既反映出当前中国非常明显的发展阶段特点——如政府主导的经济赶超,也表现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性特征——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赶超客观上要求经济资源更多流向公共部门;而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权结构,这包括大量国有企业以及公有土地等,使得政府存量资产规模庞大。
金融风险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和风险。中央由此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就金融风险而言,一方面,经过3年多的治理,风险得以缓释,防风险攻坚战取得初步成绩;另一方面,中国总体金融风险仍处在高位,且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门集中的态势。
1,“去(稳)杠杆”政策缓释金融风险
宏观杠杆率是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因此,“去(稳)杠杆”取得实效,使得总体金融风险有所缓释。第一,从金融杠杆率来看。金融杠杆率的峰值出现在2016年年底,近3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无论是从资产方数据,还是从负债方数据来衡量,2019年的金融杠杆率均已明显回落至2013年左右的水平。在金融“去杠杆”政策下,银行表外业务明显收缩,影子银行规模大幅下降。经过三年的专项治理,影子银行野蛮生长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截至2019年年底,广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84.8万亿元,较2017年年初100.4万亿元的历史峰值缩减近16万亿元。风险较高的狭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39.14万亿元,较历史峰值缩减了12万亿元。第二,从实体经济杠杆率(即宏观杠杆率)来看。从2016年到2019年年底,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包含某些时段的“去杠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因此也是“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在“去杠杆”政策的作用下,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第一季度的160.4%下降到2019年年底的151.3%,三年间下降了9.1个百分点,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2,中国总体金融风险仍处在高位,且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门集中的态势
从规模上看,在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1%,与全球杠杆率(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273.1%非常接近,但高出新兴经济体杠杆率(208.4%)61.7个百分点。疫情冲击导致中国总体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
从结构上看,金融风险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门集中的趋势。这可以分别从资产端与负债端来考察。资产端分析。基于本书设定的假设,以各部门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来衡量该部门风险承担情况,得出2018年的风险分布:居民部门占比为9.4%,企业部门占比为13.8%,政府部门占比为17.7%,金融机构占比为54.5%,国外部门占比为4.6%。其中,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风险承担比重处在前两位。考虑到中国金融企业绝大部分为国有经济性质,再加上即便是民营金融机构,最终也有一个政府救助问题,因此相关风险损失最终还是要由政府买单。假定金融机构的80%都由政府来兜底,那么,最终政府部门所承担的金融资产风险为61.3%。负债端分析。2018年中国实体经济总债务中,居民部门占比为21. 8%,企业部门占比为63.1%,政府部门占比为15.1%。我们的估算表明,国有企业债务占企业部门债务的比重从2015年年初的57%上升至2018年年底的67%。依此数据,2018年公共部门所承担的债务风险约为57.4%,这与从资产端进行的分析是比较接近的。因此,无论是从资产端分析,还是从负债端分析,广义政府或者说公共部门承担的金融风险都占到六成左右,说金融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亦不为过。
存量视角下的“存量改革”
我们一般将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称作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是指在不根本触动传统体制的情况下,在体制外发展。因此,增量改革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但存量改革完全不同。存量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难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一部分人的福利改进往往会带来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损失。所以,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以“进入”的方式来推进增量改革,那么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则是以“退出”的方式来推进存量改革。回到国家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存量改革,主要涉及财富存量和债务存量的调整,以及从动态角度重塑增量与存量的关系。
1,财富存量的优化配置
就中国而言,政府配置的资源涵盖政府代表国家和全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市场价格扭曲、配置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因此,需要推进存量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第一,自然资源方面,要以建立产权制度为基础,实现资源有偿获得和使用。第二,国有经济方面,要完善退出机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第三,推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第四,改革“科教文卫”,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2,存量债务处置与“可持续”债务积累模式
在存量债务结构中,国有企业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是“大头” (这也是债务风险向政府部门集聚的主要“体征”),是债务处置的重点。国有企业债务。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国有企业债务占比达六成到七成。因此,国有企业处置是企业部门“去(稳)杠杆”的关键。首先,由于这里有不少是融资平台债务,原本属于政府债务范畴,但2015年生效的《预算法》不予确认。建议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中也要覆盖这一块。其次,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化解部分国有企业债务。最后,“僵尸国企”的有序退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存量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僵尸国企”的退出,不仅可以消解部分债务,释放出一定的社会资源,而且也为新企业的进入腾出了空间,有利于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地方政府债务。一是扩大地方债券发行量,不仅是用于弥补当年的赤字,减少增量的隐性债务;还将用于置换存量的隐性债务(如融资平台债务)。二是盘活政府存款。2019年年底中国政府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加上财政性存款)为33.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4.4%。这一庞大规模的存款也显示出中国政府财政资金的运行效率有限。三是通过地方政府资产(如地方国企等)的处置,部分化解债务风险。
“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中国经济的赶超体制,同样也是当前中国杠杆率(特别是公共部门杠杆率)高企的体制根源。因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以及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会在中央政府担保或兜底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导致信贷扩张“任性”,激励与行为方式发生扭曲,从而形成大量的债务积累和风险集聚。由此可以判断,正是因为政府干预(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扭曲了风险定价,使得更多信贷资源流向公共部门,这是债务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的根本原因。因此,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包括打破“国企信仰”,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法为继,这样才能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